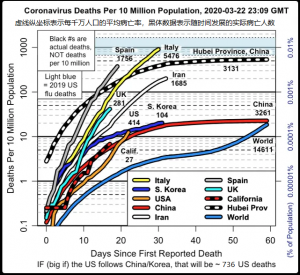罗马——当意大利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超过400例、死亡人数到达两位数时,执政的民主党党魁发了一张“在米兰举着开胃酒”碰杯的照片,劝人们“不要改变自己的习惯”。
那是2月27日。不到10天后,当感染人数到达5883例、死亡233例时,这位民主党党魁尼古拉·津加雷蒂(Nicola Zingaretti)又发了一段新视频,这回是告诉意大利,他也感染了病毒。
当前,意大利统计的感染人数超过5.3万,死亡人数超过4800人,且增长速度还在加快,超过一半的感染和死亡病例来自上周。周六,官方通报了793例新增死亡,这是目前为止单日最高数据。意大利超过中国成为单日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成了这一不断变化的疫情的中心。
政府派出军队在疫情中心——北部的伦巴第地区执行封锁,这里的教堂堆满尸体。周五晚,官方加强了全国性的封锁,关闭了公园,禁止包括远离住处的散步、跑步等户外活动。
周六晚,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宣布了又一严厉措施,以应对他所说的该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意大利将关闭工厂和所有非绝对必需品的生产,这是为遏制病毒和保卫生命做出的巨大经济牺牲。
“国家在此,”他努力安抚公众。
意大利的惨剧现在也给它的欧洲邻国和美国拉响了警报,病毒在这些地区的传播速度同样迅速。如果说我们可以从意大利的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那就是需要尽早隔离感染区域和限制广泛的人口流动,并且绝对明确到位,然后严格执行。
尽管目前采取了全球最严厉的一些措施,在最关键的疫情蔓延早期,意大利官方为了保护基本公民自由和经济却走了不少弯路。
意大利兵来将挡式的逐步性尝试——刻意留有余地的封锁,先是隔离城镇,然后隔离大区,最后关闭全国——总是比病毒的致命轨迹慢了一步。
“现在我们直追其后,”卫生部副部长桑德拉·赞帕 (Sandra Zampa)说,在当时所掌握的信息条件下,意大利已经尽力了。“我们进行了逐步关闭,与目前欧洲的做法一样。法国、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做法也一样。每天关一点,每天放弃一点正常生活。因为病毒不允许正常生活。”
一些官员心存幻觉,不愿意及时做出痛苦的决定。而与此同时,病毒得益于这种傲慢。
意大利以外的政府现在有重蹈覆辙的危险。但不像意大利是首个探索未知领域的西方民主国家,其他政府并没有多少借口可以找。
意大利官员则为自己的应对进行辩护,强调说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他们认为,政府的应对迅速有力,都是在科学家的建议下及时做出的,并且比欧洲同侪更为迅疾地采取了严厉的、对经济具有破坏性的举措。
但追踪他们的行动记录,却能发现他们错失了一些机会,并犯下一些严重失误。
在关键的疫情早期,孔特与其他高级官员试图将威胁最小化,因此制造了混乱和错误的安全感,使病毒得以传播。
他们将意大利的高感染率归咎于北部地区对无症状人群的主动检测,他们说这样做只是制造了恐慌,并让该国的国际形象受损。
即使当意大利政府认为有必要全面封锁以遏制病毒时,也未能足够有力地将威胁传达给意大利民众,说服他们遵守那些似乎漏洞百出的规定。
“对于自由民主的国家来说,这并不容易,”世卫组织委员会成员、卫生部顾问瓦尔特·里恰尔迪 (Walter Ricciardi)说,他声称意大利的行动都是基于现有的科学证据。
他说,与欧洲邻居和美国相比,意大利政府采取行动的速度要快得多,对这一威胁的态度也要严肃得多。
然而,他也承认,卫生部在说服政府同事加快速度时遇到阻碍,而在罗马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之间进行权衡调动的难度,也造成了命令传达的断裂和信息相互矛盾。
“在疫情这样的战争时刻”,那个系统会出现致命的问题,他说,同时指出这有可能推迟了限制措施的实施。
“换做是我会提早10天实行,这是唯一的区别。”
不会轮到我们
对于新冠病毒来说,10天可以是一生。
1月21日,当中国官员警告瞒报病例的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时,意大利的文化与旅游部部长在圣塞西莉亚国立音乐学院以一场音乐会接待中国使团,启动意中文化和旅游年。
推动意大利与中国关系发展的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米歇尔·杰拉奇(Michele Geraci)与在场政界人士喝着酒,眼睛却不安地看着周围。
“真的要举办吗?”他说他这样问其他人,“我们今天应该来这里吗?”
事后看来,意大利官员说当然不该。
卫生部副部长赞帕说,回头来看她会立即采取全面关闭措施。但在实时情况下,事情并不那么清晰。
各方政客都为经济和养活国家人口而担忧,并且面对病毒,他们发现很难承认自己的无力。
最重要的是,赞帕说,意大利并没有将中国看作切实的前车之鉴,而是“像看一部与己无关的科幻电影”。而当病毒爆发后,她说,欧洲“以同样的目光看着我们”。
但早在1月,一些右派官员就催促他们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政敌孔特,对北部一些从中国度假回国的学童进行隔离,以保护学校。这些学童很多来自中国移民家庭。
众多自由派公民认为该提议是散布民粹主义恐惧。孔特拒绝了这项提议,并回应说,北方地区的省长应当信任教育与卫生官员的判断,而据他说,这些官员并没有这样的提议。
但孔特也表明,他对疫情很重视。1月30日,他停飞了所有与中国之间的来往航班。
“我们是采取这项预防性措施的首个欧洲国家。”他说。
之后的一个月内,意大利对新冠病毒恐慌做出了迅速应对。两名中国游客和一名从中国归来的意大利人在罗马一家著名的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因为一起误报,官方短暂禁止停靠罗马附近的一艘邮轮上的乘客下船。
一号病人,超级传播者
2月18日,在伦巴第大区洛迪省小镇科多尼奥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一名出现了严重流感症状的38岁男子前来就诊,但该病例并未引起警觉。
病人拒绝住院并回了家。后来病情加重,几个小时后他回到医院,被送进了普通病房。2月20日,他进了重症监护室,病毒检测呈阳性。
被称为一号病人的该男子,一个月来活动频繁。他至少参加过三次晚宴,踢球练球,当时他还没有出现严重症状,但具有传染性。
里恰尔迪说,意大利的不幸之处在于,在一个人口稠密、充满活力的地区出现了一个超级传播者,去医院不止一次,而是两次,感染了数百人,包括医生和护士。
里恰尔迪说:“他非常活跃。”
但是他与中国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专家怀疑他是从另一个欧洲人身上感染了这种病毒,这意味着意大利没有可确认的零号患者,也没有可以追踪的传染源以帮助遏制病毒。
专家说,在那时,这种病毒已经在意大利活跃了好几个星期,经由无症状者传播,而且经常被误认为是流感。它在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大区蔓延,这里是与中国贸易量最大的地区,而米兰是意大利最具文化活力的商业中心城市。
流行病学专家法布里齐奥·普雷里阿斯科(Fabrizio Pregliasco)说:“我们所谓的‘一号病人’搞不好是‘200号病人’。”
到了2月23日周日,感染人数超过130人,意大利动用警察、部署军事检查站封锁了11个城镇。威尼斯狂欢节最后几天的活动被取消。伦巴第大区学校停课,博物馆和电影院关门。米兰人冲进了超市。
但是,就在孔特再次赞扬意大利的强硬手段的同时,他也试图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将感染人数多归因于伦巴第的过度检测。
他在电视上说,“我们是最早采取最严格和最准确控制手段的国家之一。”还说,意大利的感染人数多是因为“我们进行了更多的检测”。
第二天,随着感染人数超过200人、7人死亡时,股市暴跌,孔特和他的卫生助理加强了措施。
矛盾的信息播下了混乱的种子
领导人的安慰令意大利人感到困惑。
2月27日,津加雷蒂发布了他举杯的照片。同一天,意大利外交部长、执政党之一的五星运动党前领导人路易吉·迪马约(Luigi Di Maio)在罗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在意大利,我们的风险从流行病变成了信息流行病。”迪马约说,批评强调传染病威胁的媒体报道,并补充说,只有“0.089%”的意大利人受到隔离。
在距离疫情暴发中心仅数英里的米兰,市长贝佩·萨拉(Beppe Sala)开展了“米兰不停步”(Milan Doesn’t Stop)运动,并重新开放了吸引众多游客的地标性大教堂米兰主教座堂。人们外出了。
但在米兰的大区政府总部六楼,伦巴第大区重症监护病房协调员贾科莫·格拉塞利(Giacomo Grasselli)看到上升的数字,很快意识到如果疫情继续,就不可能治疗所有病人。
他的团队努力将病人匹配到最近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对越来越捉襟见肘的资源进行调配。
在一次约有20名卫生系统和政治官员参加的每日例会上,他向大区主席阿蒂利奥·丰塔纳(Attilio Fontana)介绍了数字不断增加的情况。
一名流行病学家展示了感染曲线。该大区口碑甚佳的卫生系统正在面临一场灾难。
格拉塞利告诉与会者:“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政府开始提供经济援助,随后又提供了250亿欧元(约合28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济计划。但在看到威胁的人和未看到威胁的人之间,该国陷入了分裂。
赞帕说,大约在那个时候,政府得知威尼托区的病毒疫情中心沃镇(Vò)的感染与科多尼奥的疫情没有流行病学关联。
她说,卫生部长斯佩兰扎和孔特对下一步的措施进行了讨论,并在当天决定关闭北部大部分地区。
在3月8日凌晨2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当7375人检测呈阳性、366人死亡时,孔特宣布了一项非常举措,在拥有约四分之一意大利人口的北部地区实行旅行限制,该地区是该国的经济引擎。
当时,孔特说:“我们正面临紧急状态。一个国家紧急状态。”
同时,有些区主席单独下令,要求从新划禁区来的人进行自我隔离。有些则没有。
伦巴第大区的限制实际上也解除了对科多尼奥和其他与最初疫情有关联的“红色区域”城镇的隔离。检查站不见了。当地市长抱怨,他们的牺牲被浪费了。
一天后,也就是3月9日,当阳性病例达到9172例,死亡人数攀升至463例时,孔特加强了限制措施,并将其扩大到全国范围。
但是,一些专家说,已经太迟了。
那是2月27日。不到10天后,当感染人数到达5883例、死亡233例时,这位民主党党魁尼古拉·津加雷蒂(Nicola Zingaretti)又发了一段新视频,这回是告诉意大利,他也感染了病毒。
当前,意大利统计的感染人数超过5.3万,死亡人数超过4800人,且增长速度还在加快,超过一半的感染和死亡病例来自上周。周六,官方通报了793例新增死亡,这是目前为止单日最高数据。意大利超过中国成为单日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成了这一不断变化的疫情的中心。
政府派出军队在疫情中心——北部的伦巴第地区执行封锁,这里的教堂堆满尸体。周五晚,官方加强了全国性的封锁,关闭了公园,禁止包括远离住处的散步、跑步等户外活动。
周六晚,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宣布了又一严厉措施,以应对他所说的该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意大利将关闭工厂和所有非绝对必需品的生产,这是为遏制病毒和保卫生命做出的巨大经济牺牲。
“国家在此,”他努力安抚公众。
意大利的惨剧现在也给它的欧洲邻国和美国拉响了警报,病毒在这些地区的传播速度同样迅速。如果说我们可以从意大利的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那就是需要尽早隔离感染区域和限制广泛的人口流动,并且绝对明确到位,然后严格执行。
尽管目前采取了全球最严厉的一些措施,在最关键的疫情蔓延早期,意大利官方为了保护基本公民自由和经济却走了不少弯路。
意大利兵来将挡式的逐步性尝试——刻意留有余地的封锁,先是隔离城镇,然后隔离大区,最后关闭全国——总是比病毒的致命轨迹慢了一步。
“现在我们直追其后,”卫生部副部长桑德拉·赞帕 (Sandra Zampa)说,在当时所掌握的信息条件下,意大利已经尽力了。“我们进行了逐步关闭,与目前欧洲的做法一样。法国、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做法也一样。每天关一点,每天放弃一点正常生活。因为病毒不允许正常生活。”
一些官员心存幻觉,不愿意及时做出痛苦的决定。而与此同时,病毒得益于这种傲慢。
意大利以外的政府现在有重蹈覆辙的危险。但不像意大利是首个探索未知领域的西方民主国家,其他政府并没有多少借口可以找。
意大利官员则为自己的应对进行辩护,强调说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他们认为,政府的应对迅速有力,都是在科学家的建议下及时做出的,并且比欧洲同侪更为迅疾地采取了严厉的、对经济具有破坏性的举措。
但追踪他们的行动记录,却能发现他们错失了一些机会,并犯下一些严重失误。
在关键的疫情早期,孔特与其他高级官员试图将威胁最小化,因此制造了混乱和错误的安全感,使病毒得以传播。
他们将意大利的高感染率归咎于北部地区对无症状人群的主动检测,他们说这样做只是制造了恐慌,并让该国的国际形象受损。
即使当意大利政府认为有必要全面封锁以遏制病毒时,也未能足够有力地将威胁传达给意大利民众,说服他们遵守那些似乎漏洞百出的规定。
“对于自由民主的国家来说,这并不容易,”世卫组织委员会成员、卫生部顾问瓦尔特·里恰尔迪 (Walter Ricciardi)说,他声称意大利的行动都是基于现有的科学证据。
他说,与欧洲邻居和美国相比,意大利政府采取行动的速度要快得多,对这一威胁的态度也要严肃得多。
然而,他也承认,卫生部在说服政府同事加快速度时遇到阻碍,而在罗马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之间进行权衡调动的难度,也造成了命令传达的断裂和信息相互矛盾。
“在疫情这样的战争时刻”,那个系统会出现致命的问题,他说,同时指出这有可能推迟了限制措施的实施。
“换做是我会提早10天实行,这是唯一的区别。”
不会轮到我们
对于新冠病毒来说,10天可以是一生。
1月21日,当中国官员警告瞒报病例的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时,意大利的文化与旅游部部长在圣塞西莉亚国立音乐学院以一场音乐会接待中国使团,启动意中文化和旅游年。
推动意大利与中国关系发展的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米歇尔·杰拉奇(Michele Geraci)与在场政界人士喝着酒,眼睛却不安地看着周围。
“真的要举办吗?”他说他这样问其他人,“我们今天应该来这里吗?”
事后看来,意大利官员说当然不该。
卫生部副部长赞帕说,回头来看她会立即采取全面关闭措施。但在实时情况下,事情并不那么清晰。
各方政客都为经济和养活国家人口而担忧,并且面对病毒,他们发现很难承认自己的无力。
最重要的是,赞帕说,意大利并没有将中国看作切实的前车之鉴,而是“像看一部与己无关的科幻电影”。而当病毒爆发后,她说,欧洲“以同样的目光看着我们”。
但早在1月,一些右派官员就催促他们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政敌孔特,对北部一些从中国度假回国的学童进行隔离,以保护学校。这些学童很多来自中国移民家庭。
众多自由派公民认为该提议是散布民粹主义恐惧。孔特拒绝了这项提议,并回应说,北方地区的省长应当信任教育与卫生官员的判断,而据他说,这些官员并没有这样的提议。
但孔特也表明,他对疫情很重视。1月30日,他停飞了所有与中国之间的来往航班。
“我们是采取这项预防性措施的首个欧洲国家。”他说。
之后的一个月内,意大利对新冠病毒恐慌做出了迅速应对。两名中国游客和一名从中国归来的意大利人在罗马一家著名的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因为一起误报,官方短暂禁止停靠罗马附近的一艘邮轮上的乘客下船。
一号病人,超级传播者
2月18日,在伦巴第大区洛迪省小镇科多尼奥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一名出现了严重流感症状的38岁男子前来就诊,但该病例并未引起警觉。
病人拒绝住院并回了家。后来病情加重,几个小时后他回到医院,被送进了普通病房。2月20日,他进了重症监护室,病毒检测呈阳性。
被称为一号病人的该男子,一个月来活动频繁。他至少参加过三次晚宴,踢球练球,当时他还没有出现严重症状,但具有传染性。
里恰尔迪说,意大利的不幸之处在于,在一个人口稠密、充满活力的地区出现了一个超级传播者,去医院不止一次,而是两次,感染了数百人,包括医生和护士。
里恰尔迪说:“他非常活跃。”
但是他与中国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专家怀疑他是从另一个欧洲人身上感染了这种病毒,这意味着意大利没有可确认的零号患者,也没有可以追踪的传染源以帮助遏制病毒。
专家说,在那时,这种病毒已经在意大利活跃了好几个星期,经由无症状者传播,而且经常被误认为是流感。它在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大区蔓延,这里是与中国贸易量最大的地区,而米兰是意大利最具文化活力的商业中心城市。
流行病学专家法布里齐奥·普雷里阿斯科(Fabrizio Pregliasco)说:“我们所谓的‘一号病人’搞不好是‘200号病人’。”
到了2月23日周日,感染人数超过130人,意大利动用警察、部署军事检查站封锁了11个城镇。威尼斯狂欢节最后几天的活动被取消。伦巴第大区学校停课,博物馆和电影院关门。米兰人冲进了超市。
但是,就在孔特再次赞扬意大利的强硬手段的同时,他也试图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将感染人数多归因于伦巴第的过度检测。
他在电视上说,“我们是最早采取最严格和最准确控制手段的国家之一。”还说,意大利的感染人数多是因为“我们进行了更多的检测”。
第二天,随着感染人数超过200人、7人死亡时,股市暴跌,孔特和他的卫生助理加强了措施。
矛盾的信息播下了混乱的种子
领导人的安慰令意大利人感到困惑。
2月27日,津加雷蒂发布了他举杯的照片。同一天,意大利外交部长、执政党之一的五星运动党前领导人路易吉·迪马约(Luigi Di Maio)在罗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在意大利,我们的风险从流行病变成了信息流行病。”迪马约说,批评强调传染病威胁的媒体报道,并补充说,只有“0.089%”的意大利人受到隔离。
在距离疫情暴发中心仅数英里的米兰,市长贝佩·萨拉(Beppe Sala)开展了“米兰不停步”(Milan Doesn’t Stop)运动,并重新开放了吸引众多游客的地标性大教堂米兰主教座堂。人们外出了。
但在米兰的大区政府总部六楼,伦巴第大区重症监护病房协调员贾科莫·格拉塞利(Giacomo Grasselli)看到上升的数字,很快意识到如果疫情继续,就不可能治疗所有病人。
他的团队努力将病人匹配到最近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对越来越捉襟见肘的资源进行调配。
在一次约有20名卫生系统和政治官员参加的每日例会上,他向大区主席阿蒂利奥·丰塔纳(Attilio Fontana)介绍了数字不断增加的情况。
一名流行病学家展示了感染曲线。该大区口碑甚佳的卫生系统正在面临一场灾难。
格拉塞利告诉与会者:“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政府开始提供经济援助,随后又提供了250亿欧元(约合28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济计划。但在看到威胁的人和未看到威胁的人之间,该国陷入了分裂。
赞帕说,大约在那个时候,政府得知威尼托区的病毒疫情中心沃镇(Vò)的感染与科多尼奥的疫情没有流行病学关联。
她说,卫生部长斯佩兰扎和孔特对下一步的措施进行了讨论,并在当天决定关闭北部大部分地区。
在3月8日凌晨2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当7375人检测呈阳性、366人死亡时,孔特宣布了一项非常举措,在拥有约四分之一意大利人口的北部地区实行旅行限制,该地区是该国的经济引擎。
当时,孔特说:“我们正面临紧急状态。一个国家紧急状态。”
同时,有些区主席单独下令,要求从新划禁区来的人进行自我隔离。有些则没有。
伦巴第大区的限制实际上也解除了对科多尼奥和其他与最初疫情有关联的“红色区域”城镇的隔离。检查站不见了。当地市长抱怨,他们的牺牲被浪费了。
一天后,也就是3月9日,当阳性病例达到9172例,死亡人数攀升至463例时,孔特加强了限制措施,并将其扩大到全国范围。
但是,一些专家说,已经太迟了。
最后编辑: 2020-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