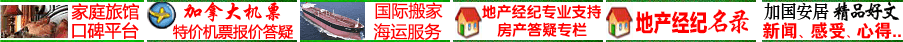回复: 柠檬花园温哥华分部
[ZT]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的下一代: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崔卫平 丁东 夏业良 郭于华 王东成
编者按
1952年,美国影响正如日中天的《党派评论》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题目是《我们的国家与文化》。目的是“考察美国知识分子用新方式看待美国及其体制的明显的问题。”去年秋天,另一杂志召集知识分子作了一场讨论,这次的题目叫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政治和文化都是关系紧张的竞技场不管这紧张关系预示了民族复兴、衰落还是维持原样。
数字技术改变了大部分美国人获得信息、相互交流和娱乐的方式,但许多人担心它将把所有形式的表达琐碎化,担心美国人普遍遵循的那些价值观随着原子化的个体而溃散,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
我们看上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联系”紧密了,博客、twitter、微博,及各种即时通信工具,都在使我们“唾手可得”。但我们却又感觉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松散了,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民间社会,各说各话,看似彰显多元价值,但事实上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这个国家和她的苦难仍然使我们不能不对潜在的危险持以警惕,担以责任。
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唤起最深沉的哀痛和历史责任感?恐怕没有比我们的下一代遭受人为灾难更让人心痛和无力的了,也没有什么比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更容易达成共识了。这是几位知识分子一次自发的讨论,无组织无预谋,他们谦虚地称,不敢妄称代表知识分子,但发出的,的确是作为知识分子之一员的声音。直面近期这些巨大的人为灾难,恐怕是包括媒体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应有的道义责任。
我们无处可逃,我们也不想推诿遁形,能做的,就是告诉你我他,社会不是“我他们”结构,而是“我们在一起”。
PART1 不能让社会变成“高压锅”
崔卫平: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直接的原因就是最近频频发生的校园学童和幼儿园孩子被砍杀的事情,这是近期最重大最突出的事情,它太大了,需要我们一起来谈谈。我个人几次提笔,每次都觉得没有力量甚至没有力气去面对这种事情。这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个社会总是有罪恶的手,伸向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最为脆弱的生命。
对于行凶的个人,没有任何可以原谅之处。然而一连串的事件,它像瘟疫一样正在流传,不应被看成仅仅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它们像病灶,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潜流。这些个人,此前多数没有暴力犯罪的历史,周围的人们说起来,都会说想不到这个人会做出这种事情。
想想看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暴力?那是在他的语言失去效力之后。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他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他需要有人听进去他所说的,对他的话有反应,让他感到自己被吸收被接纳了。而如果长时间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任何人愿意听进去他的表达,那么他便可能处于彻底的绝望状态,因绝望而虚无,而疯狂。
暴力是无声的,这个人已经很长时间处于“无声状态”了,这有可能成为暴力的诱因。这些行凶的人们当中有医生,也有教师,这些职业都是养育和扶持生命的,最终这些人反过来对幼小无辜的孩子下手。这个现象太反常了,这个问题太大了,背后的东西太沉重了。
夏业良:最近连续发生的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性事情,如果我们把它们仅仅看做犯罪现象,可能会低估它们对社会的持续的破坏力。单纯地指责当事人,说他道德方面丧失了基本的人伦,这个没有错,但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中短短几年时间里会突发那么多事件?我们讲“改革开放”的30年,其实这四个字里面对“改革”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界定,但“开放”是大家比较接受的共通的理念,开放了社会就会有进步,但不是一开放就一帆风顺一直开放下去。
比如在刚开始搞市场化改革的那些年份里,大家总的来讲还是对明天有一种更好的期望,觉得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社会在一天天进步,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连对明天的憧憬都快丧失了,觉得明天不一定是美好的。
丁东:中国古人治水有两个思路,鲧的思路就是堵,最后失败;禹的思路是疏,他成功了。治理国家,也面临两种思路的选择。
现在偏向于鲧的思路,我认为回到禹的思路比较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余年来,上世纪80年代有大禹治水之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开放言路,减少了敌人,缩小了对立面,化解了很多社会矛盾,使国家出现了中兴景象。
前几年,有些事件的处理还比较得体,不是强力地支持冲突两极的一端,而是站在两极中间,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现在有些地方官似乎又回到了鲧的思路,以堵截求稳定。
所以人们看到恶性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恶性事件具体地考察,每件事都有具体的起因。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治理得像高压锅似的,那就要从总的思路上反思了。高压锅还有一个排气阀。如果连排气阀都堵死了,就有爆炸的危险。
PART2 中国对心理疾病和精神病认识不清
夏业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要加以重视,一方面是中国人的精神疾病,按照西方精神病学的标准我们是大大低估了,我们只把那种武疯子当作需要控制的,把他们送精神病院,并强制服用抑制性药物,控制其行为;但是对数量庞大的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碍患者却置若罔闻,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心理临床医师。
另一方面,比如对待上访人员,某些部门对上访人员所采取的则是另外一种手段。其实上访人员并没有危害社会,没有激烈行为,但某些部门把本来可以挽救的、通过心理诊断抚慰,可以引导的行为激化了,就是缺失一个最后通道。
很多人之所以作出极端行为,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最后通道,如上诉的通道,或者是表达情绪、不满,提出诉求的通道,无论是网络空间还是现实世界,都彻底堵死了。两个通道都堵死的话,这个社会到底是越维越稳还是越维越不稳啊?它会激发很多人的情绪。
不用说普通人,就连知识分子当他实在没有表达渠道时,知识分子都可能在语言的强度、烈度方面表现得越来越强,包括我本人,有人问过去怎么没见你那么强烈地表达?你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激烈的言行?你们这些人这么猛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有西方在支持你们还是你们个人家庭出现了哪些不幸啊?我说都没有。而是容忍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再忍了。
郭于华:这些事件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大家看到这类案件往往把责任归咎于个体身上:精神病啊、反社会人格、极端暴力倾向等等,想到此就为止了,但是有没有更早的信号值得注意呢?如夏老师所说的,在发疯之外,就是我们称为精神分裂之外的那些心理病症,是否得到了疏导?
实际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个人性的同时就是社会性的,其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社会根源或者说社会弊端。一些人利益受损,表达无门,上访被当成精神病等,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反社会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的社会性根源。
这些施害者所为是非理性的,岂只是非理性,完全是疯狂、暴力、血腥的,而这类极端性的背后是绝望,绝望带来的是内心极度的扭曲、极度的黑暗。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中绝望的不是几个人,而是很多人都绝望,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PART3 绝望导向的丛林社会
王东成:从表征上看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事件,要是法律事件就简单了,谁犯罪就处罚谁。从这些恶性事件中能看出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全社会的绝望感越来越严重了,许多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希望,没有盼望,没有未来,痛苦感很强。
一个社会向上走的时候,会形成一些积极、健康的共识性的东西,大家都有盼望,都愿意活下去,都愿意为活下去恪守一些什么。相反,如果大家都感到自己受损害、受压抑,而受损害、受压抑又得不到解决,得不到缓解,久而久之,就会感到没希望,心理就会发生畸变,就会产生“我不活谁也别想活”、“我活不好谁也别想活好”的非理性变态心理,这样整个社会也就“失范”了。我看,发生这些恶性事件的原因,就在于制度安排不给人以希望和盼望。
如果公民的表达受到抑制,没有表达自由哪来的尊严?没有信仰的自由哪来的尊严?没有行动的自由哪来的尊严?没有公正、平等哪来的尊严?这些现象是中国人当下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郭于华:而且这个可怕在于,伤害常常指向弱者。杀害孩子事件后有家长打出旗号:“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是英雄去杀贪官,不要杀孩子”。这个报复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威权之下人们惧怕权力、崇拜权力,不敢触动权力,也无力去触动那个权力,因而就引发我们一直在谈的问题:为什么是孩子?为什么又是孩子?为什么总是孩子?孩子是这个社会中最弱小、最脆弱的。这就成为强者抽刀向弱者,弱者抽刀向更弱者这样一个逻辑。弱肉强食,这就成了丛林社会了,这是特别可怕的东西。
王东成:所以只好铤而走险,因为他没有团体的帮助。(郭于华:这还不是铤而走险,如果真铤而走险他就直接找加害于他的人了。)
PART4 人性的溃败在社会溃败之后
夏业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暴力事件,还有一个现象是现在自杀事件也非常多。自杀也属于心理上比较懦弱的,当他(她)没办法克服时,就会选择这种逃避方式:眼不见心不烦。还有一种是抑郁症,离精神崩溃不远了。这与文化程度还有关系,文化程度越高的比例越高。现在很大比例的人是这样,这样的人再往前激化一点就有可能成为无法控制自身行为的人。
崔卫平: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社会溃败”被广泛接受了,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词说明这种现象,就是“人性的溃败”或者“人性的全面倒退”,倒退到反常,这发生在社会溃败之后。
我们说人性中那些基本的东西,有关生命的基本信念,对生命的信任、信赖(你信赖自己的生命就会对他人生命有同样的感觉),其中必然包含一些基本价值,都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一旦拥有了生命,他就自然会拥有尊重、怜惜、同情这样一些基本感觉。但是现在的情况仿佛是反着来的。
我听一个心理专家说过,一个人当他想要杀人和具体地去杀人,是两回事。他想杀人是脑子想,但要真杀人看到冒血他会有一个当下的反应,他连续砍很多人,而且是幼儿,他都没有当下的基本的人性反应,可见他的人性溃败、失败、倒退到什么程度。
我都不用“恶”来形容这种情况,恶还是有形状的,恶还是个什么东西,而这种缺乏基本人性反应的人,他整个失掉了人的形状,他的人性就一点框架都没有,他就整个溃败。(郭于华:没有形状就意味着没有边界,没有底线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有形状的,文明(语言、秩序)都是赋予人以形状,而这些行凶的人们,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的人性,变成一团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一团疯狂的混乱。
PART5 精神价值的崩溃亟需社会自救
王东成:社会崩溃最根本的还是精神价值的崩溃,在这种状态下,人都不能体面地工作和生活。总书记胡锦涛不是在“五一”节表彰劳模的讲话中说,要劳动者体面地工作吗?我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我的破房子,“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可是,地方无赖就要进,就要扒你的房子。没办法,没法活,就只好把自己烧掉算了,用这种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这些人没有什么尊严。
崔卫平:让我们还是尽量把话题围绕在眼下的这件事情上,这个事情太特殊了。社会学家提出“社会的溃败”是特别有意义的。很长时间之内,我们对于“社会”这个词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而一个共同体的组成,除了从上到下这个垂直的面向,还有一个水平的面向,这就是“社会”的面向。人们之间不通过权力,而互相面对,互惠、互助和互救。任何人都会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但是他周围有一个网,能够在他最为艰难的时候,将他托起来。这个网络包括亲人,朋友,单位上的人,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这是属于一个人自己的那个小社会。(郭于华:这就是社会支持网络socialsupport)
一个良性的秩序,应该容忍水平面向各种关系的存在,包括各种结社,宗教的或者非宗教的,人需要有一些社会归属,在一定范围之内得到承认和接纳。现在对于这个水平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基本上是采取排斥打压的态度。那么人越孤立,价值观越容易模糊,因为得不到周围人的支持。
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一方面需要呼吁上下要通气,民间的声音要传到“上面”,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呼吁社会本身应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起点,不同的联合的团体,以便一个人不至于孤立到非要走上那样一条道路。
PART6 刚性维稳消灭了社会缓冲地带
夏业良:我觉得官方的不明智在于他们消除了一个社会缓冲地带,这个社会缓冲地带应该包括像宗教和民间慈善组织等社会救助力量,宗教可以帮助缓解你心理上的压力,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譬如基督教营造一种氛围: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而中国官方特别忌讳民间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它觉得你很危险,非把你纳入官方体制之内,实际上消除了中间的缓冲地带。一个社会如果存在这个缓冲地带,它就可能化解一些矛盾冲突。
郭于华:公民社会实际上是能起到这个(缓冲)作用的,公民社会越强大,发育得越好,这个社会其实是越稳定的。而没有中间的这个公民社会,刚性的稳定是很脆弱的,说出问题就出问题。咱还不说公民社会,就是刚才卫平说的这些公民的自组织,很多时候被地方官员视为洪水猛兽。
王东成: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是个人自由,一个是群体自治。没有群体自治的个人自由非常脆弱。这么多年思想解放的一个成果,就是意识到公民社会的建设太重要了。公民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提升自己。郭于华:现在的情形是一些权力打着社会建设的旗号在占领社会空间,在侵占社会。现在的“社会建设”,一方面是增加政府机构,如成立社工委等,典型地是冲着社会去的;各种各样的维稳办遍地开花,你说它这腿要伸多长吧?这与公民社会的建设完全是南辕北辙。
崔卫平: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你就是最好的动机和出发点,也不可能包办代替所有的问题,满足所有的要求。
说实话,每回听到年幼的孩子受到伤害,作为一个成年人,都会感到非常可耻。
PART7 民间信仰的重建应鼓励
丁东:人们需要精神支柱,需要终极关怀。宗教在民间发展很快,但有些人担心这会分散他的权威,分享他的权力,总想阻止这种趋势。其实,凡是教会比较发达,信众较多的地方,公众的心态比较平和,道德比较善良,犯罪比较少,社会恶性事件也比较少。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优于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王东成:举一个例子就说清楚了,温州是经济很发达的地方,温州甚至出现了民间和官方的关系都比较松弛。我知道凡是有宗教信仰比如基督教信仰的地方,人的心理状态就好得多。至少有发泄的地方,比如星期日做礼拜,听牧师讲怎么做好人等。
郭于华:民间信仰也有同样的作用,至少人们相信你做了坏事还天打五雷轰呢。多神信仰都能起制约作用,但社会把这些全部作为封建迷信搞掉了。所谓无法无天指的是什么?法是法律,天就是信仰啊。
夏业良:宗教有不可替代的力量。在1949年之后,消灭了乡绅,本来地方的自治组织,除了行政机构,这些权威,族长,城市中的士大夫阶层,都有一定的制衡力量,可以缓和官商矛盾,也可以缓和官民之间的矛盾。把这些全部消除了,认为权力可以取代一切。
崔卫平:论及“宗教”,其实我们可以换个世俗的词汇,即“价值”。一个人如果按照良知生活,他这个人是讲价值观的;人与人要互相交流通气,这中间也有一个价值的认同和交换、认可共同价值。价值在一个团体内是共同的价值。而实际上所有这些反而都被认为是危险的,不管是有价值的个人还是小团体,甚至被视为危险的来源,是要提防的对象。
王东成:奥巴马给29个死难矿工的悼词说得多好,学生都大受感动:“我们的国家怎能容忍人们仅仅因为工作就付出生命。”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正常地在幼儿园里生活,我们的学生正常地在学校里上课就得失去生命?我认为应该问责。仅仅把学校门口把住,完全不解决问题,防不住。
夏业良:刚才讲的问责,当这么多群体性事件发生,孩子被残害之后,是否应有部门向民众公开表示歉意,承认失职,以后要避免这样的事件再发生。这些事件在升级,大头娃娃奶粉,毒奶粉,毒疫苗,一步步在升级,现在已经到了直接刀砍了,要从根源上实施变革,否则等于放弃下一代。